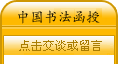魏碑,本来是古代书法由汉隶向楷、行书体演化的一个过渡书体,上承魏晋时期的原始演化,下启六朝后期的楷、行诸体日渐独立,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更替,也成为一种象八分、章草一样相对独立的一代书法艺术。
东汉时期,隶书笔法已逐渐变异。由五凤二年刻石以前的汉隶笔法渐趋八分隶体,过去书体扁平,横画起伏,竖画斜欹,微生波磔,形成左右分背之势的八分风格。本来这种变化可直达楷、行等新书体的诞生。但书法的发展象其它艺术一样,也有着曲折。八分发展到汉末三国时期,一方面有向楷体进化的趋向,一方面又回复到前期的方正之势,波磔由放纵而改为收敛,如汉末的“石经碑”、“谯敏碑”等等。这是文化意识整体固有的波动特点。不过,这种波动本身也有着发展进化的内在痕迹,一如某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呈螺旋进展之势,而每一次进展看似历史的复兴,实则新事物的萌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产生了继承古典风格又簇新独备的绘画、音乐、建筑艺术;唐代的古文运动在呼吁学习先秦古文的同时,实际上却创造了有唐以来的文学新成果。书法在三国时期的复古状态也同样地孕含着新的书体发达的步调。譬如钟繇的楷书笔意,其实完全脱胎于汉隶,仍是隶书速写的变形,是章草与八分的继续,然而,这种复古承古的书法又蕴育着时代的演化与创新,其趋向楷化的意识直接启绪了南北朝魏碑的进一步拓展,也启发了王氏代表的一代新书体的诞生。
其实,这种创新往往又在之前已有痕迹。汉末至魏的隶书,多使用逆笔,所用的毛笔也多是硬毫,如运笔有画,必先自左将笔势突进作成尖锐棱角,于停顿转折之处,微呈波磔之势。与之同时的草率书体则没有这种笔法,如作横画,落笔便过;倘用新笔,始见尖锋;用秃笔,则如后世藏锋之状。楷书、草书的起笔,就不用逆笔取势。从敦煌汉简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不同变化。书法因为书写工具和书写意识的进步,也必然有整体风格的进步。可以这么说,汉末三国时期以钟繇为代表的书法艺术,是一种逐渐自觉的新书体创造意识的表现,为后来的魏碑打下了基础。
然而,较可惜的是,魏碑由于刻石的特点和时代的因素,并没有形成楷书,而停留在近似楷书又不同于楷书,因而也独备一体的成就水平上。倒是行、楷之类,借王氏为代表的书法家由章草和钟繇的发展成就中继续粹炼,而成为真正独立的新书体。
一、魏碑产生的社会背景
文化的繁荣,往往也是艺术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反而促发了文化的兴盛,其原因一如春秋战国时期。在秦汉以来,社会统一、文艺继续繁荣的要求日益壮大,尤其怫学的昌盛,使人们心理上因战乱、地域纷争中不能实现的愿望、思想、艺术等文化心态在相对安宁的一定社会地域间得到了拓展伸延。秦汉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艺术得以大发展;到了南北朝,似乎这种发展已不可遏止。于是,在百家争鸣中必然造成文艺的复兴,必然导致社会统一后更大的文艺繁荣和发展。这已是历史发展的定势。
汉代佛学由印度传入中国,很快在表面的纷争中与儒、道、法家哲学,尤其是汉以来确立的儒家思想交融一体。由于汉代的尊儒,秦代的尚法,使道家与佛学在行政干预中争得社会一定心理上普遍承认的同时而备感压抑。到了魏晋南北朝,旧有的行政压抑因为战争而解脱,新的行政手段又因为战争难以强化,佛、道之学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便勃然兴盛。